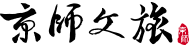| 旅游規劃設計甲級資質 |
-
010-62263429
-

-

-

Latest news
最新資訊
Latest news
最新資訊
文孟君:國家文化公園的“國家性”建構
作者|文孟君
自2019年國家出臺《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以來,“國家文化公園”業已成為文旅規劃的一個熱點話題。其中,如何在“國家文化公園”規劃建設中建構“國家性”,成為“國家文化公園”區別于普通文化旅游公園及其類似文旅景觀的必要條件。在管理體制機制方面,“方案”已經明確要“完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管理體制機制。構建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分級管理、分段負責的工作格局。強化頂層設計、跨區域統籌協調,健全工作協同與信息共享機制,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為地方創造條件”。諸如國家對于規劃編制的管理和監督,中央財政的支持,國家的“垂直管理”與地方管理相結合等等,這些都體現了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的“國家在場”。上述管理體制機制之外,“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還需要在價值觀和文化內涵等方面重視“國家性”的建構。也只有如此,才更能凸顯國家文化公園的“國家象征”,傳播其“國家品味”和“國家意味”,最終實現“國家認同”。
首先是“國家性”場景的營造。
由特里·克拉克(TerryClark)、丹尼爾·西爾(DanielSilver)為首的新芝加哥學派創立的“場景理論”,認為舒適物設施、活動和人群的組合,構成一地的“場景”,也就是一個地方(社區)的整體文化風格或美學特征。也就是說,一地的文化風格(美學特征),譬如“國家性”,取決于什么樣的舒適物設施、活動和人群的組合。依此理論,作為“國家”文化意義的體現,可以通過諸如國家歷史文化遺產的“古跡”、國家性的組織機構、“國家文化”標識、國家性的論壇會議和節慶活動、國花國鳥、國家標識色彩(如“中國紅”)等的組合,來體現國家文化公園的“國家性”場景。這些“國家性”文化元素的體現,是使國家公園與非國家公園,以及其他景觀得以區別的鮮明表征。
其次,“公共物品”擴大供給和“志愿組織”的跨界發達。
“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哥倫比亞大學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Wimmer)教授在其《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中認為,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國家建構的兩面。國家建構至關重要的是建立公民與國家間的跨越族群分界線的政治聯系,將各族群整合進一種包容性的權力安排之中。基于社會交換網絡的視角,威默認為國家與公民間的交換關系有三個方面:如何組織;交換資源;溝通協商。因此,發達的志愿性組織,較強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國家能力,以及較低的語言溝通障礙這三個條件,有助于政治聯盟網絡實現跨越族群界限的擴展,支持國家認同的構建。
作為國家文化公園,“公共物品”的擴大供給,體現在國家公園的“全民公益性”。國家文化公園作為一種公共文化產品,實現保護傳承、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游觀光、休閑娛樂、科學研究功能,為公眾提供游憩、觀賞和教育的場所,讓全體公民(尤其是相關社區及其居民)享受國家公園的福利,使民眾感受自然人文之美,接受自然、生態、歷史、文化教育,培養國民愛國情懷,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
這種“公益性”,也體現在“全民參與”度。公眾既是國家公園的主要受益者,更是積極參與者。調動公眾參與國家公園保護傳承的積極性,在自然人文的感召下主動參與建設管理,擁有建設管理的知情權、監督權。這種“全民參與”將會提高國家文化公園的管理質量和效率。
因此,相關國家文化公園的發達的“志愿組織”,將是“國家性”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志愿組織”群體,來自五湖四海,族群、性別、年齡多元,心性志趣、職業背景各異,文化層次高低不同,但因應“國家文化公園”這一話題而結成各類“志愿組織”,跨越族群等界線,以各自視角、理念、體驗來參與探討和實踐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這樣的“志愿組織”發展情況,充分體現了社會公眾的參與熱情和對國家文化公園的關注度,自然,也就體現了國家文化公園的獨特魅力和引領地位。
第三,文化內涵的共享。
國家文化公園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載體,承載著國家代表性的中華文化內涵,是國家的象征,體現了中華民族夢想創造、團結奮斗的精神。這些優秀文化精神理應走向民眾,與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為民共享,成為民眾集體認同的國家文化記憶。
這就需要國家文化公園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軌,與時代精神相融合,創新文化場景,完善展示體系,凸顯整體標識,強化傳播效果,實施標志工程等,使民眾于日常生活中接觸“國家品味”的文化形象,體驗“國家在場”感,從而感悟“國家意味”。
第四,可見的日常生活。
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國家起源”(genesis of the state)理論,將“國家”這一概念延伸到了現代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用“國家起源”來表述國家通過一系列活動來建構自己的行為。國家通過具有表征性的活動來建構自己,這些表征性活動是國家空間擴張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家是一個具有隱形性的不可見的實體。國家雖然不可見,但是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來表征自己。這些表征活動將使國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識中。(王艷雪、包智明,《國家建構視角下的村落景觀變遷與生產》,《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3期)
英國社會歷史學者帕特里克·喬伊斯(Patrick Joyce)、錢德拉·穆克吉(Chandra Mukerji)從物質過程與實踐的角度,也提出基礎設施等物質多地點的連接、重組而構成國家,并使得國民產生國家系統的觀念。也就是說,國家不僅是“想象的共同體”,更是可見的日常生活,是分布各地的政府大樓、公路、運河、城市設施、公共空間等的網絡連接。(《The state of things: state history and theory reconfigured》,《Theory andSociety》46,1–19(2017))
因此,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與相關區域內外的公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那些事關公眾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等物質,構成民眾的日常生活圖景,而這些圖景又成為“想象共同體”國家的表征,形成國家形象,最終建構起國家“認同”。
總之,在國家文化公園這一偉大景觀生產中,“國家性”的建構,既有宏大景觀的營造,又有日常生活的保障;既要國家努力供給“公共物品”,又要公眾“全民參與”的“志愿組織”,由景觀建構意義,由意義重塑景觀,這樣的文化公園才符合公眾的國家想象。
京師文旅
集合文旅融合戰略研究及文旅項目策劃與實操、國家A級景區/國家旅游度假區創建全程輔導、鄉村振興及農旅項目落地與運營、文創產品研發及衍生應用、培訓參訪及投融資服務等五大業務板塊,傾力打造:“美好生活旅游目的地”內容提供商。